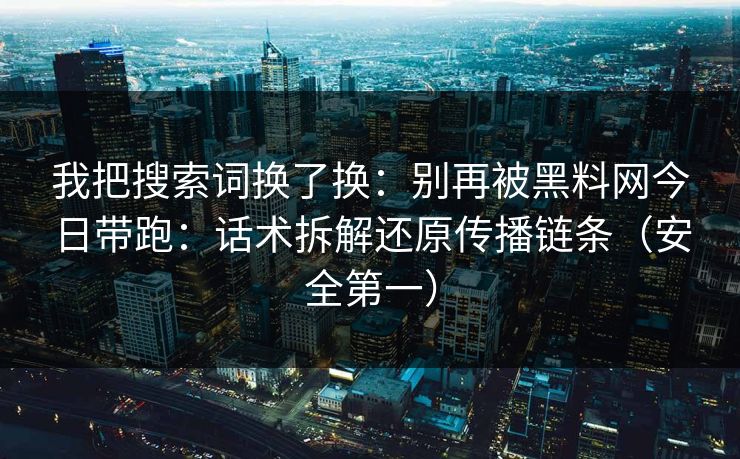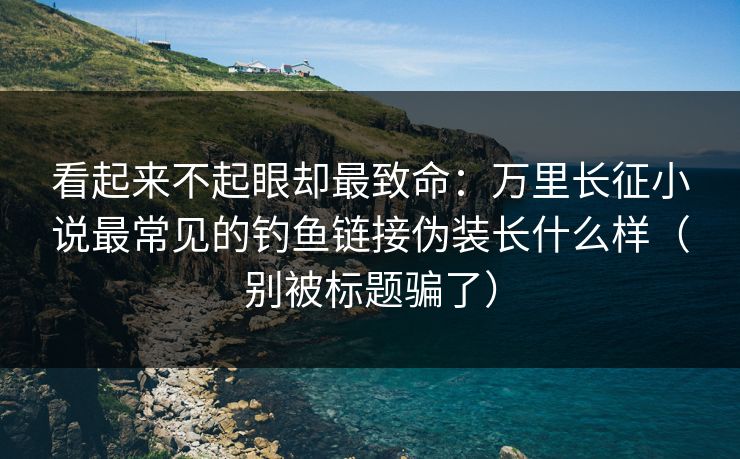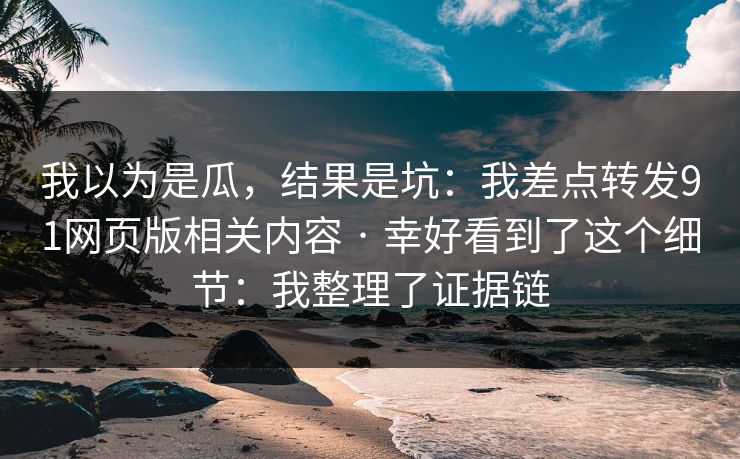红烛烬·暗涌的棋局
雪落在破败的宫檐上,像一场无声的祭奠。十七岁的云蘅公主褪下最后一件珠钗,望着镜中苍白却依旧锐利的眉眼,轻轻笑了。亡国那天,父王的血溅上她的裙摆,三个男人的身影立在烽烟尽头——北境枭雄萧彻、南疆世子谢珩、西域军师玄知。他们各自执棋,而她成了棋盘上最诱人的筹码。

「公主可知,活下来的方式从来不止一种?」玄知的羽扇轻摇,声音如蛇信擦过耳际。他将她献给萧彻,换得西域三万铁骑按兵不动。萧彻的军营里篝火熊熊,这个男人用战袍裹住她冻僵的脚踝,眼底却毫无温度:「你是我最锋利的刀,亦是最暖的榻。」
而谢珩在月下递来一柄淬毒的匕首:「杀了他,我许你南朝后位。」他笑得温润,指尖却掐得她腕骨生疼。云蘅在三个阵营间辗转,每夜撕下染血的绷带时都觉得自己像一朵被反复碾碎的花。但她藏在枕下的,不止有匕首和毒药,还有父王临终前塞给她的虎符暗纹——半块能调动前朝暗军的玉珏。
玄知教她权术,萧彻授她武艺,谢珩赠她诗书。他们以为驯服了她,却不知她早已将计就计。当萧彻压着她后颈逼问玉珏下落时,她咬破他的嘴唇轻笑:「王爷若真想找,不妨先挖了我的眼——毕竟它们曾替你辨过敌军阵图呢。」
暗流汹涌的第九个月,北境王帐突然起火。云蘅在混乱中盗走边防图,转身却撞见玄知倚着焦柱把玩火折子:「公主这出戏,臣添把火如何?」他永远这样,笑着将所有人推向更深的深渊。而那夜救她出火海的人,是本该在南疆的谢珩。
「三个疯子。」云蘅抹掉颊边血迹,在驿站的铜镜前缓缓描画柳眉。镜中映出的不再是亡国公主,而是蛰伏的凰鸟。
凤凰啼·终局与新生
玉京城的桃花第三次开败时,天下已成三分之势。萧彻控北境,谢珩据南朝,玄知掌西域。而云蘅站在废弃的观星台上,指尖摩挲着终于拼合完整的虎符。这三年来,她利用萧彻的兵力截杀谢珩粮草,借玄知的密道向南朝输送假情报,更在谢珩赠她的诗集中破译出前朝藏宝图。
「玩火终会自焚。」玄知扣住她手腕那夜,西域正飘着罕见的雪。他眼底第一次没了笑意:「公主可知,我原本真想过与你共赏江山?」她抽回手轻笑:「军师错矣。是我要不要与你共赏。」虎符坠地之声清脆,暗处涌出的铁甲寒光灼穿了雪幕。
最终的对峙发生在父王殒命的大殿。萧彻的剑抵着谢珩喉咙,谢珩的弓弩瞄准玄知心口,而玄知的毒针悉数没入萧彻肩胛。三人浑身是血,却仍死死盯着殿门外的云蘅——她提着前朝玉玺,身后是黑压压的复国军。
「诸位教我的。」她踏过凝固的血泊,声音清冷如刃,「棋手沦为棋子时,最该砸了棋盘。」
萧彻大笑咳血:「早该掐断你这株毒花!」谢珩折断箭矢苦笑:「我竟真信过你会选我……」唯有玄知缓缓拭去唇边血迹,仰头看她时眼中有奇异的光彩:「成王败寇。但公主,你烧北境王帐那夜,我本是去救你的。」
云蘅没有回答。她亲手将三枚玄铁锁链扣上他们的手腕,却在转身时坠下一滴泪,迅速湮没在尘灰里。史书只会记载:前朝云蘅公主铁血复国,收北境、平西域、纳南朝,终登帝位。至于那三个被囚于摘星塔的男人——有人说女帝常独坐塔下斟酒,有人说听见塔中传来琴剑相和之声,更有人说曾在月夜见到四道身影并肩立于塔顶,如江山图上最浓墨重彩的一笔。
红颜乱世,终究乱的是人心,还是世道?或许唯有摘星塔顶那坛百年陈酿,才尝得尽其中滋味。